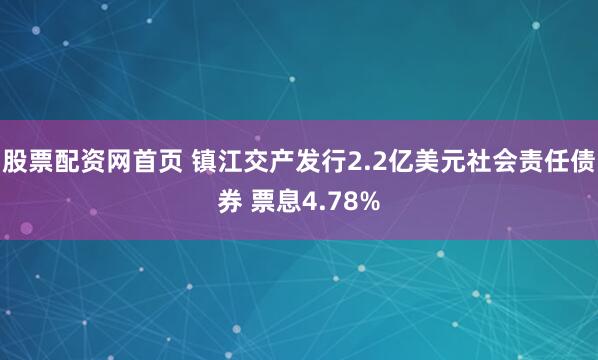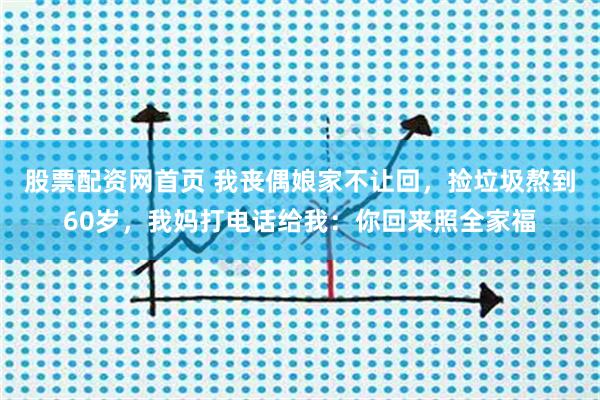
冰冷的雨水混着垃圾桶酸腐的气味股票配资网首页,浸透了黄月兰单薄的衣衫。
这二十年,每一个瑟缩在桥洞下的夜晚,她都会想起那个被娘家决绝关上的门。
丧偶的悲痛未曾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被至亲抛弃的刺骨冰寒。
她从昔日备受呵护的黄家女儿,变成了城市角落里一个无声的影子,靠着拾荒,熬过了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。
岁月粗糙的手将她打磨得如同路边的石头,直到那通几乎被她错过的电话响起。
母亲苍老而熟悉,却又带着一丝陌生疏离的声音穿过电流:“月兰啊……你回来吧,家里要照张全家福。”
第一章:被关闭的门
黄月兰永远记得那个秋天的傍晚。
天色灰蒙蒙的,像一块脏了的抹布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她拖着沉重的脚步,怀里紧紧抱着丈夫李建国的遗像,身后是一个小小的、褪了色的行李箱。
展开剩余95%那里装着她和丈夫短短五年婚姻里所有的甜蜜和依靠,如今,只剩下这些冰冷的物件。
丈夫的猝然离世抽干了她所有的力气和希望。婆家本就清贫,办完丧事,更是容不下她这个“外人”,言语间的挤兑和冷漠,让她明白那里已无她的立锥之地。
走投无路之下,她只能想起娘家。那个她出生长大,曾以为无论何时都会接纳她的港湾。
娘家的院门似乎比她记忆中要新一些,也冷漠一些。她抬起颤抖的手,敲响了门。
开门的是她的大哥黄卫军。他看到门外的她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眉头紧紧皱起,脸上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,只有毫不掩饰的厌烦和为难。
“月兰?你怎么回来了?”他的声音干巴巴的,堵在门口,丝毫没有让她进去的意思。
“哥……”黄月兰的声音沙哑,带着哭腔,“建国他……他没了。婆家那边,我待不下去了……”
她的话还没说完,母亲的声音就从屋里传了出来,尖利而清晰:“卫军,谁啊?堵在门口干什么?”
黄月兰心里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,她试图绕过大哥看向里面:“妈,是我,月兰!”
母亲的身影出现在大哥身后。她穿着干净的藏蓝色褂子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她看着黄月兰,眼神复杂,有瞬间的惊愕,但很快被一种更坚硬的东西覆盖了。
那是嫌弃,是怕被拖累的恐惧。
“月兰啊,”母亲开口了,声音里听不出多少温度,“不是妈狠心,你也知道,家里就这点地方,你弟弟马上就要说亲事了,你这时候回来……像什么样子?”
黄月兰的心一点点沉下去,沉进冰冷的深渊。她抱着遗像的手指用力到泛白:“妈,我可以睡客厅,我可以出去找活干,我不会白吃饭的……”
“找活干?你能干什么?”大哥不耐烦地打断她,“一个寡妇,回来住着,街坊邻居怎么说?你弟还要不要娶媳妇了?赶紧回你婆家去!”
“哥,婆家我真的回不去了……”泪水终于决堤,黄月兰几乎要跪下去哀求。
母亲别开了脸,声音冷硬: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你的根在你婆家,不在这儿了。我们黄家,没有让寡妇回门长住的道理,不吉利。”
最后三个字,像三根冰冷的针,狠狠扎进黄月兰的心脏。
“妈……”
“走吧走吧!”大哥开始推搡她,“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,让人看了笑话!”
那扇曾经为她敞开的家门,在她面前被重重地关上了。砰的一声巨响,隔绝了所有的光和希望,也彻底斩断了她与这个家的最后一丝温情。
她甚至能听到门内传来母亲压低声音的训斥:“赶紧把她弄走!”以及弟弟黄卫民模糊的应和声。
黄月兰僵在原地,怀里的遗像冰冷地贴着她的胸口。秋风吹起地上的落叶,打着旋儿,像是在嘲笑她的无家可归。
世界那么大,却没有一寸地方愿意容纳她。
从那一刻起,她知道自己真的只剩下一个人了。
第二章:废墟里的微光
最初的几天,黄月兰像是失去了魂魄。
她漫无目的地在城市的边缘游荡,饿了就掏出口袋里最后几块干硬的饼子啃两口,渴了就去找公共厕所的水龙头灌一肚子凉水。
夜晚降临是最难熬的时刻。桥洞、废弃的房屋、甚至街心公园的长椅,都成了她暂时的栖身之所。寒冷和恐惧如影随形,每一个细微的声响都能让她惊坐而起。
身上的钱很快用尽了。生存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悲伤和屈辱。她开始留意路边那些被丢弃的瓶瓶罐罐和纸皮。
第一次伸出手去捡拾一个脏污的塑料瓶时,她的脸颊烧得滚烫,手指颤抖不已,仿佛周围所有人都在用鄙夷的目光注视着她。
但饥饿和寒冷是更强大的老师。很快,她学会了低着头,避开人群的目光,专注于那些能换回一点点钱币的“宝藏”。
她弄来一个破旧的编织袋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赶在清洁工之前翻遍一个个垃圾桶。恶臭、污秽、旁人的驱赶和白眼,成了她生活的常态。
她的手很快变得粗糙开裂,指甲缝里塞满了洗不掉的黑泥。曾经白皙的脸庞被风吹日晒得又黑又糙,皱纹过早地爬上了她的眼角。
她几乎不再说话,像一座沉默的礁石,承受着生活一浪接一浪的无情拍打。
就这样,一天天,一月月,一年年地熬着。时间失去了意义,只剩下日出和日落,以及每天能否多捡到几个瓶子。
在一个同样寒冷的冬日清晨,黄月兰在一个大型垃圾堆放点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时,遇到了邓容。
邓容看起来比她年纪更大些,头发花白而凌乱,用一根脏兮兮的布条草草捆着。她动作却很利索,正麻利地将一些硬纸板踩扁捆好。
两人同时看中了一个被压扁的纸箱,几乎同时伸出手。
邓容抬起眼,看了看黄月兰。黄月兰下意识地想缩回手,准备离开。她习惯了退让,不与人争抢。
但邓容却先开口了,声音沙哑却 oddly 平和:“这个你拿去吧。那边还有几个。”
黄月兰愣住了,有些不知所措。
邓容没再说什么,只是继续忙自己的。但从那天起,黄月兰发现她总是能在这个区域“偶遇”邓容。
邓容会默默地分她一些捡到的食物,虽然常常是些发蔫的蔬菜或磕碰过的水果。会在下雨时,示意她到同一个废弃的窝棚下躲雨。会在有管理者来驱赶时,低声提醒她快走。
她们很少交谈。邓容似乎也不爱说话,只是偶尔会嘟囔几句天气,或者抱怨一下最近能卖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。
但这种无声的、保持距离的互助,像一丝微弱的火苗,温暖着黄月兰早已冻僵的心。她知道了这座城市里,并非只有彻底的冰冷。
她知道了邓容也是年轻时丧夫,无儿无女,被亲戚霸占了房子后,流落街头,靠拾荒已经活了十几年。
“习惯了就好,”有一次,邓容看着远处的高楼,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,“人嘛,怎么不是活。”
黄月兰没有接话,只是低下头,更用力地压紧手中的纸板。是啊,怎么不是活。只是这“活”法,太过艰难,磨掉了她作为人的最后一点体面和期盼。
她就这样,靠着捡垃圾,一天天地熬着。熬走了青春,熬走了健康,熬走了对亲情所有的幻想。
她看着城市日新月异,高楼拔地而起,而她却像被遗忘在时代缝隙里的尘埃,慢慢地、无声无息地滑向衰老和腐朽。
她熬到了六十岁。
第三章:陌生的声音
六十岁生日那天,没有任何人知道。
黄月兰像过去的几千个日子一样,在天蒙蒙亮时醒来,从她那个用塑料布和硬纸板在废弃排洪渠边搭起来的、勉强称为“家”的窝棚里钻出来。
她的关节僵硬酸痛,尤其是膝盖和手指,每逢阴雨天就疼得厉害,这是长年累月风寒和劳损留下的印记。
她捶了捶腰,开始整理前一天捡到的“收获”,分类捆好。动作熟练却缓慢,岁月到底是不饶人。
邓容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没能熬过去。人们发现她时,她已经在那个小窝棚里僵硬了,表情很平静。
黄月兰默默处理了邓容留下的一点微不足道的遗物,继续着一个人的挣扎。失去这唯一的“熟人”,她的世界更加寂静了。
下午,她拖着那一小捆废品,去往熟悉的废品收购站。路上经过一个热闹的社区广场,一群穿着鲜艳的老人正在音乐声中跳着广场舞,孩子们笑着追逐嬉闹。
她远远地看着,眼神麻木,仿佛在看另一个世界的故事。那种鲜活的、热闹的、属于“正常”人的生活,早已与她无关。
卖掉废品,换来几张皱巴巴的零钱。她小心翼翼地将钱塞进贴身的衣兜里,这是她接下来几天的饭钱。
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,口袋里那个老旧的、屏幕早已模糊不堪的二手按键手机,突然响了起来。
铃声刺耳又突兀。
黄月兰吓了一跳,下意识地捂住口袋。这个手机几乎从未响过。她留着它,只因为在最初流落街头的日子,心里还存着一丝可笑的幻想——或许娘家会后悔,会打电话来找她。
但几十年过去了,这个幻想早已破灭。知道这个号码的,只有几年前去世的邓容,但她从未打过。
谁会找她?打错了吧。
铃声固执地响着,一遍又一遍。在周围嘈杂的环境音中,显得格外执着。
黄月兰犹豫着,终于还是慢吞吞地掏出手机。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号码,归属地显示是她老家的城市。
她的心跳莫名漏跳了一拍。一种久违的、类似紧张的情绪攫住了她。
她颤抖着手指,按下了接听键,将手机贴到耳边。
“喂……?”她的声音因为长久不说话而异常干涩沙哑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,然后,一个苍老、疲惫,却又带着某种奇异熟悉感的女声传了过来:
“是……月兰吗?”
黄月兰的呼吸骤然停止了。这个声音……即使隔了二十年漫长的光阴,即使被岁月磨损得如此厉害,她依然在一瞬间就认了出来。
是她母亲。
她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,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手指用力地攥紧了那只破旧的手机,指节泛白。
“月兰?听得到吗?我是妈啊。”对面的声音提高了一些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和……不确定?
黄月兰张了张嘴,试了好几次,才终于从喉咙深处挤出一点声音:“……妈?”
这一个字,仿佛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。带着二十年的委屈、困苦、迷茫和无法言说的隔阂。
“哎!听得见,听得见就好。”母亲的声音似乎松了口气,紧接着,一种刻意营造的热络语气透过听筒传来,“月兰啊,这么多年……你……你还好吗?”
好吗?黄月兰看着自己龟裂的手指甲,看着身上沾满污渍的旧棉袄,看着脚下这片脏乱的土地。
她好吗?她几乎要冷笑出声。
但她最终只是沉默着。二十年的苦难,岂是一句“好吗”能问尽的。她又该从何说起?
母亲的寒暄得不到回应,似乎也有些尴尬。电话两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,只能听到电流的滋滋声和对方有些沉重的呼吸声。
黄月兰能感觉到,母亲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话要说。
果然,母亲咳嗽了一声,打破了沉默,语气变得正式起来,甚至带上了一点黄月兰记忆中从未对她有过的、近乎商量的口吻:
“月兰啊,给你打电话,是家里有件事……你弟弟卫民的儿子,就是你大侄子,下个月要结婚了。这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啊!”
黄月兰静静地听着,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侄子?她离开时,弟弟黄卫民还是个毛头小子,听说后来结了婚,生了孩子。但这些都与她无关了。她只是那个被排除在“全家”之外的“外人”。
母亲继续说着:“家里商量着,趁这个机会,照一张全家福。一大家子人,好久没聚齐了……”
她的声音顿了顿,似乎在斟酌用词,然后,终于说出了这通电话的真正目的:
“月兰啊……你回来一趟吧。回来照张全家福。”
第四章:回不去的“家”
“回来照张全家福。”
这句话像一枚投入死水的石子,在黄月兰沉寂了二十年的心湖里,惊起了剧烈而混乱的涟漪。
回去?那个在她最绝望无助时,冰冷地将她拒之门外的家?
那个她苦苦哀求,却只换来“不吉利”三个字和重重关门声的地方?
照全家福?哪里的“全家”?又有谁的“福”?
一瞬间,二十年前那个秋天的冰冷感觉再次席卷而来,比此刻身上的寒意更刺骨。她仿佛又看到了大哥不耐烦的脸,听到了母亲冷硬的话语,感受到了那扇门关闭时带起的绝望的风。
二十年了。整整二十年。
这二十年里,她像一只下水道里的老鼠,在城市的阴影里挣扎求存。她睡过寒风刺骨的桥洞,捡过馊臭的食物,被驱赶,被嘲笑,生病了只能硬扛,每一个冬天都仿佛在鬼门关前打转。
她熬白了头发,熬垮了身体,熬干了眼泪。
他们呢?她的母亲、哥哥、弟弟,他们在这二十年里,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想起她?可曾有过片刻的愧疚和不安?
没有。一次都没有。
她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,被彻底地从那个家的记忆里抹去了。哪怕她就在同一座城市的角落里慢慢腐烂,他们也从未寻找过。
现在,侄子要结婚了,需要“全家”团圆了,需要照一张看似美满完整的“全家福”了,他们终于想起她了?
想起她这个失踪了二十年、恐怕在他们心中早已死去的“寡妇”姐姐和女儿?
为什么?
黄月兰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,一股混杂着多年积怨、屈辱和强烈质疑的情绪在她干涸的心田里横冲直撞。
她几乎能想象出那幅“全家福”的画面——父母端坐中间,哥哥弟弟两家簇拥着,笑容满面,喜庆祥和。
而她呢?她站在哪里?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状态站在哪里?
一个消失了二十年,衣衫褴褛、苍老憔悴、与周围光鲜亮丽的他们格格不入的老乞丐?
她回去,是为了衬托他们的美满?是为了填补那张照片里唯一空缺的、可能被外人议论的位置?是为了让他们的“全家福”看起来不至于少一个人而显得“不完美”?
还是……另有目的?
母亲这通电话里那份刻意的热络,那份小心翼翼的语气,那份不合常理的邀请背后,到底隐藏着什么?
黄月兰握着手机,手指冰冷。电话那头,母亲听不到她的回应,似乎有些着急了。
“月兰?你在听吗?能回来吗?车费……车费家里给你出!”母亲急急地补充道,仿佛这是一种天大的恩赐。
车费?黄月兰几乎要笑出眼泪。她这二十年的人生,难道就差这一张车票钱吗?
她缺失的是温暖,是接纳,是在绝境中能拉她一把的手,而不是在一切尘埃落定、他们需要妆点门面时,施舍般的一张“入场券”。
她的沉默让电话那头的母亲越发不安。
“月兰啊,过去的事……就让它过去吧。”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,带着一种含糊其辞的意味,“终究是一家人,血脉亲情是断不了的。你侄子结婚是大事,你这当姑姑的,总得露个面……”
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?”黄月兰在心里无声地重复着这句话,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,重新剖开她心上从未愈合的伤口。
她说得多么轻巧。那几乎毁掉她一生的伤害,那二十年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苦难,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“过去”了?
她的痛苦,她的挣扎,在她至亲的人眼里,原来是可以如此轻易被“过去”两个字抹杀的吗?
那么,她这二十年又算什么?一场无足轻重的噩梦?
电话那头,母亲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,说着侄子有多出息,对象家境多好,这场婚礼对家里多重要,全家福多么有必要……
每一个字,都像是在黄月兰沸腾的情绪上浇油。
她回去干什么?
去扮演一个他们需要的、久别重逢、阖家团圆的工具人?
去用她狼狈不堪的现状,反衬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?
去让她这二十年所受的苦,变成一个轻飘飘的、可以一笑置之的“过去”?
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悲哀。
她想要对着电话嘶吼,想要质问,想要把二十年的委屈和痛苦全都倾泻出去。
但她张了张嘴,却发现喉咙被更坚硬的东西堵住了。
她只是死死地咬着牙,听着母亲在那头规划着“全家福”该怎么拍,谁该站在哪里,仿佛她已经答应回去,仿佛她理所当然地应该配合这场演出。
从那天起,她就被排除在那个“家”之外了。
从那天起,她就只是黄月兰,一个孤零零的、挣扎求生的拾荒老太婆。
现在,他们凭什么用一个“全家福”的名义,就想轻易地把这一切抹去?就想把她重新拉回那个框架里,扮演一个她早已不再熟悉的角色?
母亲的声音还在继续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安排口吻:
“就这么定了,月兰。你赶紧收拾一下,明天就买票回来。地址没变,还记得吧?全家福就等着你来了!”
第五章:尘封与伤疤
黄月兰最终还是回来了。
不是第二天,而是在一种极其复杂和混乱的心绪中,拖延了好几天。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回来。或许是想亲眼看看那个曾经抛弃她的家变成了什么样,或许是想看看那些亲人的脸上是否会有一丝愧疚,又或许……只是心底最深处,那一点点对“家”的残存渴望,像灰烬里的火星,未曾彻底熄灭。
她用攒了很久、藏得最深的那点钱,买了一套最便宜但还算干净的衣服,仔细地(尽管收效甚微)清洗了自己,试图洗掉一些常年积累的风霜和痕迹。
坐在长途汽车上,她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,感觉一切都陌生得不真实。越靠近老家,她的心跳就越快,手心渗出冰冷的汗液。
下车,按照记忆中的路线走。街道变了,楼房多了,但大致方向还在。
那座熟悉的院门果然还在,甚至比二十年前更气派了些,贴了新的瓷砖。她站在门口,久久没有勇气去敲门。
仿佛二十年前那扇门关闭的巨响,还在耳边回荡。
终于,她抬起沉重的手,敲了敲门。
开门的是个陌生的年轻女人,打扮时髦,疑惑地打量着她:“你找谁?”
黄月兰张了张嘴,还没回答,母亲的声音就从屋里传了出来:“是不是月兰回来了?”
母亲的身影出现在年轻人身后。她老了很多,头发几乎全白了,背也有些驼,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。看到黄月兰,她脸上瞬间堆满了笑容,但那笑容看起来有些夸张,有些不自然。
“哎呀!真是月兰!快进来快进来!”母亲热情地招呼着,一边对那年轻女人说,“小薇,这是你大姑,快叫人。”
年轻女人——黄卫民的儿媳,上下扫了黄月兰一眼,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和疑惑,勉强叫了声:“大姑。”然后就让开了门。
黄月兰僵硬地迈过门槛。院子也翻新过了,铺了水泥地,角落还种了花草。屋里传来了说话声,听起来人不少。
她被母亲拉着进了堂屋。屋里瞬间安静下来。
沙发上坐着父亲,比母亲显得更苍老,眼神浑浊,看到她,只是微微点了点头,没说话。大哥黄卫军也在,发福了不少,挺着个啤酒肚,看到她,眼神有些闪烁,点了点头,算是打过招呼。弟弟黄卫民和他妻子也在,同样带着一种审视和客套的笑容。
还有几个年轻人,应该是侄子侄女辈的,都用好奇而陌生的目光看着她。
整个屋子,宽敞明亮,家具崭新,和她那个破旧的窝棚天差地别。但她却感到一种比在垃圾堆旁更甚的窒息感。
她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异类,格格不入。
“快坐,快坐,一路上累了吧?”母亲热情地安排她坐下,递过来一杯水。水是温的,但黄月兰握在手里,却觉得冰凉。
话题很快围绕着即将到来的婚礼和全家福展开。他们讨论着去哪家照相馆,穿什么衣服,什么时候去。他们说得热火朝天,但黄月兰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,被排除在这热烈的讨论之外。
他们偶尔会问她一句“是吧,月兰?”或者“大姑觉得呢?”,但那眼神分明不是真的征求她的意见,只是一种客套的流程。
没有人问她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。没有人对她表示一丝一毫的关心和歉意。仿佛她只是出门旅居了一段时间,如今按时回来了而已。
那种刻意营造的“正常”和“亲热”,比直接的冷漠更让她感到刺痛和虚伪。
她看着母亲忙碌地张罗,看着哥哥弟弟们谈笑风生,看着侄子侄女们玩着手机。她感觉自己像一个道具,被摆放在这里,等待着完成“全家福”的任务。
拍摄全家福的日子到了。
一大早,母亲就拿出了一套新衣服,塞给黄月兰:“换上这个,照出来精神点。”
那衣服的款式和颜色,显然不是黄月兰这个年纪和气质会穿的,更像是为了配合整体色调而统一安排的戏服。
黄月兰默默地接过。
就在她准备换上的时候,听到弟媳在门外低声对母亲抱怨:“……她那头发乱糟糟的,脸色也太差了,这样照出来多难看?要不让她站边上去,或者后期让照相馆的人给P一下?”
母亲压低声音回答:“行了,少说两句,赶紧弄完就行了。忍一忍。”
“忍一忍”。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黄月兰的耳朵里。
原来她的存在,是需要被“忍”的。原来她的模样,是会破坏这张“完美”全家福的。
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,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。
她拿着那件崭新的、却像枷锁一样的衣服,猛地拉开了门。
门外,母亲和弟媳吓了一跳,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
黄月兰看着她们,看着闻声望过来的哥哥弟弟,看着这一屋子光鲜亮丽的“家人”。
她的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,但声音却异样地平静,带着二十年风霜磨砺出的砂砾感:
“你们叫我回来,就是为了这个?”她举起手里的衣服,“就是为了让我穿上这个,像个傻子一样,站在你们旁边,证明你们一家团圆、幸福美满?”
母亲脸色变了:“月兰,你胡说些什么呢!快把衣服换上,照相馆约好的时间快到了……”
“我不换。”黄月兰打断她,声音不高,却异常清晰,“我也不照。”
“你!”大哥黄卫军皱起眉头,习惯性地想拿出当年的威严,“你闹什么脾气?大老远叫你回来,不就是为照张相吗?多大点事!”
“多大点事?”黄月兰看向他,眼神里是积压了二十年的冰与火,“对你们是小事。对我不是。”
她深吸一口气,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:“二十年了。你们谁问过我一句,我这二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?谁问过我一句,我吃不吃得饱,穿不穿得暖,生病了有没有人管?”
屋子里鸦雀无声。侄子侄女们也放下了手机,惊讶地看着这个突然爆发的大姑。
“你们没有。”黄月兰自问自答,声音哽咽却强忍着不掉泪,“你们觉得我丢人,觉得我不吉利,把我关在门外的时候,想过我是家人吗?现在需要照全家福了,想起我来了?让我回来,就是为了让你们的面子上好看一点,不是吗?”
“月兰!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!”母亲提高了声音,带着窘迫和恼怒,“现在不是好好的吗?一家人团团圆圆的……”
“我们从来就不是一家人!”黄月兰终于吼了出来,眼泪也随之夺眶而出,“从你们把我关在门外那天起,就不是了!我的家人不会在我丈夫死了无家可归的时候不要我!我的家人不会让我像个乞丐一样在外面自生自灭二十年!”
她指着这宽敞的屋子,指着他们身上光鲜的衣服:“你们过得真好,真幸福。真好。但我这二十年,是靠捡垃圾活下来的!捡垃圾!你们知道吗?你们在乎过吗?”
“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?”弟弟黄卫民忍不住开口,语气不耐烦,“都过去那么久了,又不是我们逼你去捡垃圾的?你自己没本事怪谁?”
“卫民!”母亲呵斥了他一声,但已经晚了。
黄卫民的话像一把尖刀,彻底捅破了那层虚伪的窗户纸。
黄月兰看着他,忽然笑了起来,笑得凄凉而绝望:“对,我没本事,怪我。怪我命不好,克夫,怪我没出息,活该被娘家扫地出门,活该捡垃圾……所以,我现在也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了,不破坏你们‘全家福’的团圆气了。”
她把手里的新衣服重重地扔在地上。
“这相,你们自己照吧。少我一个,没什么区别。”
她说完,转身就往外走。
“月兰!你给我站住!”母亲在她身后气急败坏地喊。
但黄月兰没有回头。她一步一步,坚定地走向门口。这一次,是她自己要离开这扇门。
第六章:迟来的“馈赠”#优质图文扶持计划#
就在黄月兰的手快要碰到门把手的时候,母亲突然冲了过来,一把死死拽住她的胳膊。
“你不能走!”母亲的声音尖利,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急切,完全失去了之前的伪装,“你走了不行!”
黄月兰用力想甩开她,但母亲枯瘦的手指却像铁钳一样箍着她。
“放开!”黄月兰冷声道。
“不行!你不能走!”母亲几乎是在嘶吼,脸色涨红,“你走了,那钱怎么办!那房子怎么办!”
钱?房子?
这两个词像定身咒,让黄月兰的动作顿住了。屋里其他人也愣住了,显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。
“妈!你胡说什么呢!”大哥黄卫军急忙上前想拉开母亲。
母亲却不管不顾,死死盯着黄月兰,语无伦次地说:“拆迁!老房子要拆迁了!按户口和人头算补偿!你的户口一直没迁走!算上你,我们能多分一套小户型!还有补偿款!你走了,户口本上没人,就没了!你就得回来签字!你得配合!听见没有!”
一瞬间,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。
为什么二十年不闻不问,突然热情地叫她回来。
为什么一定要照这张“全家福”——那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婚礼的面子,更是为了向拆迁办的人证明,他们家的“女儿”回来了,户口本上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,是家庭的一员,理应享有份额。
所有的温情脉脉,所有“一家人”的幌子,底下掩盖的,竟然是如此赤裸裸的、关于金钱和房产的计算。
黄月兰看着母亲因为急切和欲望而扭曲的脸,看着哥哥弟弟们脸上猝不及防被揭穿的慌乱和尴尬。
她忽然觉得无比荒谬,又无比可悲。
她笑了,笑声干涩而苍凉:“原来是这样……怪不得,怪不得啊……”
她用力一挣,终于甩开了母亲的手。
母亲踉跄了一下,被大哥扶住,却还在喊着:“你得签字!那钱和房子都有你一份!你难道不想要吗?”
“我要?”黄月兰环视着他们,目光冰冷而锐利,“我要了,然后呢?和你们继续做‘一家人’?等着你们算计完这一次,再想办法把我踢出去?”
她摇了摇头,语气斩钉截铁:“你们的钱,你们的房子,我一点都不稀罕。二十年了,没有你们,没有那些东西,我也没饿死。”
她看向母亲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户口,你们想办法迁掉也好,注销也好,随你们的便。字,我不会签。那份钱和房子,你们谁爱要谁要,与我无关。”
说完,她不再有任何留恋,毅然决然地拉开了那扇门。
门外阳光刺眼。身后传来母亲崩溃的哭喊和兄弟们嘈杂的争吵声。
但她已经不在乎了。
她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院子,走向车站,走向她来的地方。身体依然佝偻,步伐依然沉重,但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。
那根捆绑了她二十年、名为“家”的绳索,在这一刻,终于被她彻底斩断了。
她失去了血缘定义的“家”,但在此刻,她找回了自己。
黄月兰最终选择了离开,拒绝了那份迟来的、充满算计的“馈赠”。
她回到了属于她的城市角落,继续着她清贫但平静的生活。
那张没有她的全家福会如何,那份拆迁款最终归属谁,都已与她无关。
她用自己的方式股票配资网首页,为这段被强行续写的亲情,画上了一个决绝的句号。
发布于:河南省隆盛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